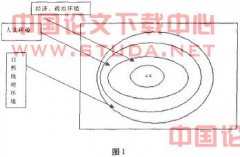【内容提要】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摘 要 题】本期专栏:当代文化研究
【关 键 词】经典化/经典/大众文本/精英文本
【正 文】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这种推崇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金庸及其作品的“经典化”,其实,在大众文本中,作者被“经典化”的不止是金庸一个人,与他具有相似命运的,还有喜剧片的导演兼演员卓别林,美国的西部片导演约翰·福特,惊险片的导演希区柯克,以及创作出了《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道尔,撰写了《飘》的玛格丽特·米切尔,以及写出了《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的张恨水等;而作品被“经典化” 的就更多了,如影片《乱世佳人》、《雨中曲》、《正午》、《克莱默夫妇》、《沉默的羔羊》及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弗兰肯斯坦》、《根》、《教父》、《人性的证明》等。被“经典化”的结果,自然是这些作品成了人们认可的“经典”之作,这些作者也就成了经典文本的创作者。但是,这里随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经典”文本?它与精英文本的区别是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从“经典”的释义开始。
“经典”(classic)一词在理论上有多种含义,也被不同的理论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从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对诸多研究者关于“经典”论述的梳理,可以看出,文本上的“经典”通常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指“最优秀”的作品,二是指被“广泛承认”的作品,三是指在文本内在特性上“复杂和不确定到了足以给我们留出必要的多元性的地步”的作品。这样三种意义上的“经典”作品,无疑主要是针对精英文本而言的,它或者指那些被评论家们誉为最优秀的作品,或者是阅读起来最复杂多义、能够与读者进行无止境对话的文本,或者是其地位已获得广泛认可的文本。事实上,历史上的经典文本也基本都是精英文本,它们被编选成文集,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写进文学史或艺术史,并进行示范性的解读,以作为“伟大的传统”供世人拜读和学习。这样的文本“经典”体系总是富于创新的作品的天下,似乎很难容得下程式化的大众文本,而大众文本仿佛也就永远与“经典”作品无缘。
其实不然,因为“经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文本价值的评估尺度或标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尺度或标准的建立以及这个尺度或标准的制定者的威权。这也就是说,一种政治、文化或者宗教威权的存在,会带来一种。尺度或标准的确立,而根据这个尺度或标准,就会遴选出一批作品成为这个威权所认可的“经典”文本。因而,美国学者弗兰克·克默德指出,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1]。而当这种威权发生动摇或者改变的时候,其作为“战略性构筑”的文本“经典”体系也会随之发生动摇和改变,于是,新的威权与新的“经典”的衡量尺度或标准会乘虚而入,逐渐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的经典作品体系。就在这种改朝换代般的变化之中,一些不被既往经典体系所认可的作品,包括大众文本,获得了“晋升”“经典”的机会。
但是,大众文本进入“经典”的重要契机,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结构下的威权的改换。因为大众文本根本就不属于传统社会,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经典”重构中,才有可能获得“经典”的提名。当然,大众文本这种提名的获得,首先是基于现代社会遴选“经典”作品尺度或标准的变化。由于“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再也不存在能够强行颁定一部经典的宗教或政治势力了”,“与此同时,文学的领地已被缩小到了不再危及现存制度的安危的境地”,所以威权“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做监督或批准经典的确立工作了”。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结构下“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一种严格的经典成为必要”的话,那么,只有当威权“放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的时候,“经典”“才能获得解放”[2]。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当然不会完全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但控制的程度显然较传统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松动,而松动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多元化社会的出现。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导致了“经典”评估尺度或标准的变化,使“经典”文本体系的成员构成也趋于多元。其次,大众文本“经典”提名的获得,是基于大众文本自身的繁荣。大众文本的繁荣兴盛使它自身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广大的接受群体——大众中,而且也波及了向来很少关注大众文本的专家学者群落,使得专家学者们已经无法漠视它的存在,进而不得不正视它、认可它,以至于研究它。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评价,无疑是大众文本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众文本获取“经典”提名,实质上是作为文本接受者的大众、专家学者以及现代社会多元化语境(其中有政治及文化威权的力量,而且是其中一种主要的力量)共同“协商”的结果。这正如有位学者在分析通俗文学时所指出的那样,“‘通俗文学’经典不是哪一个人的‘经典’,它是一个协商的结果。它是各方力量一起抬出的一顶蓝尼大轿。其中主要的力量,当然是专家们和读者大众”[3]。
多方力量“协商”的重要成果是“经典”构成元素的多样化,也就是说,“经典”不再纯粹是精英文本的“经典”体系,而是成了“收藏”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多种文本形式或种类的“仓库”。在这个“仓库”里,“经典”的“功能”得到突出的强调,或者说,文本主要是靠自身的“功能”而不是权威的支持而获得“经典”地位的。至于“经典”的功能,查尔斯·阿尔蒂瑞有过如下论述:
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教化性的(curatorical):文学经典蕴藏着丰富的,充满复杂对照的准则,它创造用以阐释经验的文化语法。但是,考虑到典范性的材料的本质,我们不能将教化性的功能仅仅看作是纯语意的,因为经典还包括价值——这种价值既存在于被保存的内容也存在于保存的原则。因而,经典的另一基本功能必须是规范性的。因为上述功能是彼此关联的,所以经典不能被表达为简单的教条,相反,作为辩证的来源,经典辨明了我们为了获取富于对比色彩的语言所需的差异,并提供了当我们支配这语言时我们自身所形成的模式,功能的相互关联转而适用于这两种基本模式,每种模式分别显示出文学作品的不同维度。经典为我们提供在文学形式内部运作的范例。经典是收藏发明的仓库,是对我们在一种文体或风格中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中,技巧不仅是其自身的目标,也是强化文本提供一种有意味的姿态的能力的方式,它使我们得以接近非文本的经验。所以在训练我们寻找功能关联的方式时,经典除确立了保存技巧范例的模式外,还确立了智慧的模式[1] 。
而正是在查尔斯·阿尔蒂瑞所论述的“经典”功能的意义上,中国学者李勇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经典’学习到该文化中一整套相关联的‘处世’经验与‘智慧模式’。就文学而言,它既提供技巧范式,也提供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这样看来,一种文化中的‘经典’应该是多样的,我们说不上哪一种作品哪一天会派上用场。因此,最好办法是把‘经典’当成‘收藏发明的仓库’。这个仓库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通俗学’这一大类”,并且还进一步指出,“就‘经典’的功能来看,如果说要让一部现代‘经典’很好地发挥其‘文化语法’与‘智慧模式’的功能,选择‘通俗文学’作品也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属于广大市民的 ”[3]。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里,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是合乎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的,也是合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及文本创作的需求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里,经典文本已经不能等同于精英文本。精英文本有着自身独特的以“创新”为标志的尺度,它也许也有很少量的模式因素,但其文本的创作宗旨与根本指向却完全在于独创,在于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它是创作个人化的结果,是创作者独特个性的表达。而经典文本在一定的意义上,不是创作的结果,而是历史、社会、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经典文本不是哪一个作家创作出来的,而是由创作者、接受者、社会政治与文化权威以及特定的历史或时代需求等力量共同推举出来的“排行榜”的榜单。在这个榜单里,有“创新”性的精英文本,可能也有“通俗”性的民间文本和“程式”化的大众文本等。也正因如此,“经典”才能成为“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用以保存各种文本的“技巧范例”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可见,经典文本,在现代社会里,已经由传统社会里的“经典文本=精英文本”的概念界定,转变成为一个“经典文本>精英文本”的概念范畴,而后者显然较前者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宽广的外延。这种转变使得“经典”一词,不再是“精英文本”的代名词,而成了一个涵盖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各种文本形式的典范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它的意义“ 所指”,也更倾向于作品“公认的”、“典范的”功能。因而,今天的“经典”,已经添加了更多的文本收藏及展示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见,本文所谓“经典”,并非大众文本内部的经典之作,而是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共同的“经典”,即将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放在一起所确立的经典文本目录。这个目录因为收藏了各种文本形式的典范性作品,而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一个民族的智慧模式以及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的象征。这个目录,不仅是诸多专家学者向社会隆重推荐并加以精心注解的作品选本,而且是被写进文学史供学生们学习的 “必读书目”,因而它是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认可的文本集群。大众文本只有进入这样一个目录,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才算真正走向了“经典”。而前文所列举的金庸、卓别林、约翰·福特、希区柯克以及柯南·道尔等人的大众作品,所走入的正是这样一个经典目录或名单。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金庸不仅被排到了中国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表中,而且对其武侠小说的分析被作为一门课程开到了中国最著名大学的讲堂上。在英国,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不仅成为世界上“除了莎士比亚和《圣经》”之外,“人们研究最多的”大众文本形象,而且已经“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歇洛克学’”[4],在国外一些专门的福尔摩斯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并在一些著名大学的课堂上加以讲授。约翰·福特、希区柯克等人及其作品走入“经典”的经历,也大致如此。
当然,能够被经典化、成为“经典”之作的大众文本,只是数不胜数的大众文本中的极少数作品。而且,这些极少数大众文本往往还必须具有某些特别素质,才能够得到“经典”的提名。关于这些特别素质,有研究者指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大众文本之所以能够被经典化,是因为达到了三条“经典”标准线。其中首要标准是“作品本身要具有较高价值”,即作品要具有“时代感”,要具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在“思想内容” 上要“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第二个标准是作品“必须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第三个标准是作品要具有“独创性”,但这种“独创性”“应该是在规范的框架中的创新”[3]。本文认为,这三个标准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其中的第二个标准和第三个标准,是决定一个大众文本能否成为“经典 ”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即只有拥有巨量规模的接受者和表现出“独创性”(这种“独创性”与精英文本的创新不同,是一种“程式中的创新”)的大众文本,才有可能走进“经典”。
在“程式”中创新的大众文本,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本。而随着一些雅俗共赏的大众文本走进“经典”,大众文本无疑也开始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认可。尽管这种认可还仅仅是初步的,是更多用精英文本尺度或标准所作的文本衡量,着重挖掘的也是大众文本中有关“创新”的那一面,或者说被“创新”之光所照亮的那个文本表现区域,至于大众文本中的“程式”因素或有关“程式”的那一面,则被遮蔽或忽视了。这一点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论述“通俗小说”的文字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说,“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俗小说在整个文学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它自身的价值。讲清楚李涵秋、张恨水乃至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他们的创作跟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他们作为通俗小说家对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这才算触及问题的实质”[5]。而就在这种忽略大众文本“自身的价值”的理论观念与实践批评中,“程式”——这个大众文本最重要、最具本体性的文本特点,成了一个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批评“盲区”。这个批评“盲区”只要还存在着,就说明一些大众文本走入“经典”的事实就还属于偶然的、特别的现象,大众文本也还没有真正得以被与精英文本同等对待,依然还在学术理论界处于弱势地位。
事实上,不认可大众文本的“程式”,就不可能真正认同大众文本。因为大众文本的“程式”与大众文本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摒弃了大众文本的“程式”,就等于摒弃了大众文本。因而,那种对大众文本的“程式”视而不见或者不屑一顾的研究者所作的大众文本研究,在本质上并不是对于大众文本的真正的科学的探究。他们将某些大众文本“经典”化,只是在“拔高”大众文本的前提下为他们的精英文本体系又选拔了一名符合当代文化价值取向的新成员而已,而在选择与评价“经典”的尺度与标准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目前不少情况下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过是一种准“经典”化,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它与我们理论设想中的那种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并予以认同、收藏的“经典”体系比较起来,还有不短的距离。
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繁盛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大众文本的地位必将得到不断的提升,那种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并予以认同、收藏的“经典”体系,也必将在某一个时候被建立起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坐标和各种文本发展的一个示范。在这个“经典”体系里,文化类型不分贵贱,平等是其精神;文本不论高下(此处的“高下”与文本质量的优劣无关,而是就文本的不同特点而言的),大众文本的“程式”与精英文本的“创新”得到同样的认可。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和哪一类文本,只要它们表达了人类(无论是“大众”还是“少数人”)的心理诉求,能够满足人们健康向上的精神需要与正常合理的欲望需求,就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显然,只有这样,这个“经典”文本体系才能够真正体现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各种文化平等的精神。
事实上,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改变既往文化及文本观念的时候了。因为在世界越来越呈现后现代色彩的当代国际社会里,以往精英文化及其文本与大众文化及其文本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被填平与跨越,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这种文本,正如詹姆逊所说,“这就是,在它们当中,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惑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包括廉价低劣的文艺作品,电视系列剧和《读者文摘》文化,广告宣传和汽车旅馆,夜晚表演和B级好莱坞电影,以及所谓的亚文学,如机场销售的纸皮类哥特式小说和传奇故事,流行传记、凶杀侦探和科幻小说或幻想小说:这些材料它们不再只是‘引用’,像乔伊斯或梅勒之类的作家所作的那样,而是结合进它们真正的本体”[6]。这种新的文本形态的出现,使得我们已经无法清晰地辨别一些文本的“精英”或“大众”性质,而只能看到其中“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日益互相渗透的文本表现(这种表现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无厘头”文本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詹姆逊看来,正是这种新的文本形态,呼唤着一种新的文化与文本的探讨与评价方式。他说,“在我看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化/大众文本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大众文化是民众的,因而比精英文化更权威;精英文化是自主的,从而与低级的大众文化不可相提并论)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的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互联系的、辩证地互相依存的现象,作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和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7]。詹姆逊的这种论述,主要是针对像美国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与文本发展状况而言的,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文化与文本现状,但中国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日趋多元的文化发展格局,在一些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及沿海地区,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了某些“后现代”社会的症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精英/大众文化”的文本。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大众文化对不少精英文本的改编或“戏说”,也能够看到融合了一定的流行元素或大众文本程式因子,但又表达了创作者鲜明个性与追求的文本的日益增多。亦即“雅俗共赏”的文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而这种“雅俗共赏”的新的文本形态的兴盛,就更加显示出了大众文化的泛化,显示出了大众文本的繁荣。
面对这种“后现代”社会症候下大众文化的泛化和大众文本的繁荣,我们的理论界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种似乎是“俯就”的应对姿态,更重要的是需要树立一种新的重新审视文本价值的观念,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新的文本存在状态的批评方式和价值评估尺度。因为只有在这种观念、批评方式和价值评估尺度下的大众文本,才能够真正以自身的特有本性与价值进驻“经典”,成为“经典”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元。也只有到那时,优秀的大众文本才能够得到理论界真正的认同,才能被安置在其应该被安置的文化地位上。
【参考文献】
[1] 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 [荷兰]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李勇.“通俗文学”的经典化[J].新世纪学刊(新加坡),2001,(创刊号):48—57.
[4] [美]托马斯.A.西比奥克,珍妮·伍米克—西比奥克.福尔摩斯的符号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和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 王逢振,盛宁,李自修.最新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